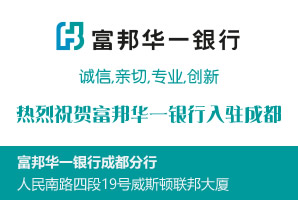李敬泽新作《青鸟故事集》: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
记:我印象里,你至少三次前瞻性地提出观点引起世人关注:一是2000年针对历史的平民史观写作;二是2008年你担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时力推“非虚构写作”;三是你对亚洲与欧洲、东方与西方的文学性想象的对比……
李:我曾经说,人类一定是相互想象的,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,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文学作品。想象会有偏差,但偏差不能阻挡我们的相互想象和交流。比如对郑成功的认识,我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他早期的抗清和后来的收复台湾,其实他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明代禁海后,民间海上活动非常活跃,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郑芝龙、郑成功海商集团。大量民间商人在正史叙述中都是“海盗”,但现在看,这些民间海商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,甚至为后来我们海上疆界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。从日本到菲律宾,从东海到南海,先民们冒着巨大的压力、风险、困难,与日本、荷兰、西班牙等国家展开激烈竞争,而且占了上风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。
元写作是一种精神
记: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?是一种由跨文体构成的“超级写作”吗?
李:从写作方法上我基本认可“超级写作”,但我未必是跨文体。准确说,我向往的是一种朝向元典的元写作,这是一种精神,不是文体学问题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问题,在《左传》里均可以找到踪迹。那是民族的元典,展示出强有力的语言与强有力的精神。可惜的是,春秋时代斩钉截铁的问题,被当代人搞得非常复杂和暧昧。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没有从元典里吸取滋养,后来因为各种训令形成的价值观就是可疑的。
如果说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展示了人类的基本问题,并且得到了可贵的延续和发展的话,那么中国的元典并没有得到一流头脑的诠释,既然如此,弘扬与继承就更无从谈起了。《青鸟故事集》是对异质经验的涉入与旁出,其现实意义可能要高于16年之前。尤其是在一个面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,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汉唐作为伟大帝国的高标,它如何与西方发生关系?
记: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吟唱?
李:我不大相信口述实录。一个人口才再好,笔头很烂,这两者没有关系。但吟唱不同。走在天地之中,心中有歌要唱。这就是文学,这就是荷马,这就是元典精神,这就是鲍勃迪伦给我们的启示:我们需要不断返回元写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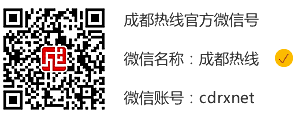
028-86612222
028-86969110 96111
028-85587777 85555046
028-88881890
028-84321999